
我们可以先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逻辑上去理解“什么是科学”,维特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科学”就是“能够说的事情”,把这能说清楚的“事情”努力去说清楚,这就是“科学”。而能说清楚的“事情”是什么呢?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也就是“大自然”,“科学”就是对具体“事物”的研究。自从出现人类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由生物的“神经系统”被感知的世界,这个系统就是指人人都具有的触觉、视觉、听觉、嗅觉等,也包括人们利用各种工具对这些“感知”系统的延伸,如显微镜。这个世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物质世界”。另一个是由人特有的发达大脑去感知的“主观”世界,也就是所谓“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分散在每个人大脑中,不存在大家都感知的“客观世界”。现实中每个人的这个“世界”只能以“话语”(包括公式、图形、图片、视频等)作为工具而进行交流,甚至没有这个“工具”也就可以认为没有这个“世界”,由此可以推理出“精神世界”也就是“语言的世界”。维特根斯坦将而这“语言世界”里又分“能说清楚的”和“说不清楚的”两类“语言文字”,“能说清楚的”是说明“物质世界”的,是建立起“物质世界”和“语言”之间的“映射”;“所不清楚的”是来自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一个人把自己的“主观世界”用语言文字传了出去,当人消亡之后,“语言文字”可以存留在“物质世界”上,它的意义只是“词语概念”或者成为他人的“客观世界”。“科学”显示在人们面前的是属于“能说清楚”的“语言文字”,是对“物质世界”的描述,与科学家是否消亡无关。
博彩公司只做彩票菠菜国际平台手机娱乐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分析可以看成是“语言的逻辑”,也就是任何语言概念,包括由词语概念组成的“话语”、“长篇著述”都和实实在在的事物有联系,这是“实”的一面;同时又不过就是“话语(概念)”,和人的“精神世界”有联系,是“虚”的。“物质世界”是人人面对的,人们也就可以用“语言”与之“映射”;而人的“精神世界”是难以说清楚,因为只是存在于个人的“内心”。但人们所处的“物质世界”要用“语言”去准确“映射”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语言”都有需要思考的一面,而每个人之间的思考能力是不一样的。“科学”就是人类面对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用语言去描述这个“事实”,最初的这类“语言”只能说是“常识”,是大部分人都理解的,是很粗糙的,随着人们努力去更简洁的语言更清晰去说明这个物质世界,虽然参与的人少了,但产生了“科学”,实现了“语言”和“现实(事实)”的准确相互映射,使人们不会对记述“物质世界”的“言论”产生争议。我们谈“什么是科学”就是分析科学语言和我们日常使用的话语有什么不同,找出科学语言的特点。
皇冠体育博彩平台邀请您参加最新的虚拟比赛,包括体育赛事、竞速游戏等,让您在享受博彩游戏的同时,还能感受到虚拟世界的无限乐趣。我们提供最专业的博彩攻略和技巧分享,让您在博彩游戏中尽情享受乐趣和收益。首先科学上使用的概念是符合形式逻辑的,说亚里士多德是科学的始祖是有道理的。科学语言使用的语言概念都有清晰的“内涵”与“外延”,语言概念是一个“集合”,而科学研究的对象是“集合”中的“元素”。现实中的任何事物是否“属于”词语概念的意义是确定的,不允许似是而非。例如日常生活中常使用“水果”这个概念,但是“西瓜”是否属于“水果”就让人有点犹豫,所以科学就不会使用这类概念。科学就是从“事实”出发,从看上去无联系的事物找出它们的共同点,经过深入思考后,发现现实中的事物彼此都是相似的,于是会产生“新概念”取代原来的概念,例如把马、牛、羊、鸡、鸭、鹅等等都归纳为“动物”;把小麦、蔬菜、树木等等归为“植物”,甚至干脆都归为“生物”。科学虽然是从“事实”出发,研究对象是现实中的事物,但说明这些事物的“词语概念”又都是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的概念。最能代表科学的学科是物理学,物理学是对“物质世界”的研究,这个物质世界是极其繁杂和多样的,但物理学把组成物质世界的一切都看成是“物体”,这个物质世界除去“物体”没有其他“东西”。“人、灰尘、星球、动物、植物……”都属于“物体”这个“集合”中的“元素”。虽然物质世界中的事物相互关联,变化复杂,但在描述事物运动的规律时,又将复杂的现实抽象成简单孤立的“物体”,谈物体运动规律,是谈“质点”、“刚体”的运动规律……,仿佛和现实是脱离的。科学是对物质世界的研究,但科学语言具有抽象性,并不是对现实的直接描述,这是因为语言完全准确描述现实是做不到的,或者说一个简单现象也需要冗长的语言去叙述。例如一列列车通过一个山洞的时间是多少?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考虑列车长度,考虑“通过”的准确含义,物理学科讨论的是对“质点”运动情况和规律的研究,忽略物体的大小问题,而不是回答“列车”运动的规律问题。
科学语言使用的概念都是严格符合数学上的“集合”原理,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这个“集合(概念)”中的“元素”,这些“元素”实际上可能大不一样,但都与同一个“概念”相互“映射”。这让我们有了对“元素”量化的可能,直接与“数学”建立起联系,实现逻辑运算。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词语概念中的“外延”,也就是“集合”中的“元素”,而不是“集合”。科学研究问题不是从“整体”上去看,而是尽可能“分解”到不能再分的程度,这都为“元素”的量化和运算提供基础。物理学中研究的对象都是“物体”,我们从各个角度去分析而产生出不少新概念,如质量、速度、能量、受力……,这些概念都又都是可量化的,是和数学有联系的。物理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极为清晰,甚至数学公式取代了文字语言,直接成了物理理论。科学的这个特征也很容易和其他讨论问题的方法相区别,不重视数学逻辑或者不需要数学作为分析问题的理论不能称之为科学。
科学中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从“事实”出发,从几乎人人知道的常识出发,不断观察、思考下去而形成低、中、高不同层次的“话语”,也就是“科学”谈论的问题一定是有层次的。当“科学”作为语言传输时,“说”者与“听”者要则是“师生关系”,要则是“商讨关系”。前者是为了得到更广泛传播,后者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科学的“语言”只能在层次相差不大的人之间传播,也就是存在“听者”能否接受的问题,这一点是学校中的科学学科教学的基本原则。任何一门“学问”是不是“科学”,从有没有清晰的“层次”也可以做出判断。这实际也是用“语言”来描述“事实”的过程,“物质世界”是可以说清楚的,但肯定还有需要进一步去认识的地方,总存在有还“说不清楚”的地方。文学艺术可以做到“雅俗共赏”,这就说明它不是“科学”。对物理学来讲,掌握牛顿力学的一般是需要有高中以上学历,而谈论相对论,谈论量子力学就是很个别人的话题了。
www.championsportshq.com太平洋在线注册皇冠源码皇冠客服飞机:@seo3687科学来自对“物质世界”的思考,最早的科学就是“常识”,随着思维的深入,科学语言和直观的“物质世界”会产生一定距离,也就是科学是一种理论,是一种“思想”。如果更彻底认识“科学”,科学就是一种“语言文字”。但科学来自“物质世界”,来自“事实”,当作为“思想”、“理论”时,也不可能与现实没有联系。故而科学是可以“证伪”的,这里的“证伪”不同于和“检验”、“验证”。科学虽然是“理论”但它是在谈“现实”,“证伪”是指没有“现实”不符合我们提出的“理论”。例如我们做惯性定理的实验,不是在做“验证”的工作,而是“我做出努力了,但找不出不符合这个定律的例子,欢迎你找出否定这个定理的例子”。这一特点是强调了凡是“理论(话语)”都来自人的“思想”,和现实是脱节的,它的“正确”与否是由谈论“理论”的人去决定,而不是“实践”;而“证伪”的意义是可以用“事实”去说明“理论”是错的,这是“科学”思考问题的方式。“证伪”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所谓的“一票否决”,不承认“特例”,这也是“理论”是不是“科学”的关键点。
有了对科学方法的认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也就是科学不是对物质世界的直接描述,而是面对物质世界产生的“思想”。“科学原理”也并不是自古至今都客观存在的“东西”。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是不准确的说法,而应该是“牛顿用极其概括的语言和精确的数学公式描述了自然界最普遍的一种现象”。没有人类,或人类并不思考,月亮仍然会绕地球转,人和其它物体一样在地球上,但绝不会有万有引力定律,更不会有物理学。科学也如同物理学一样,是人类编写出的信息,是由“语言文字”表现出来的“思想”。科学是面对“物质世界”的思考,是对“大自然”的思考,是把“人”同样视为“物体”,但用这种方法研究人类社会是做不到的。人类社会是由“人群”组成,但这个“群”不是天然的,是由于人有了语言之后产生的,我们研究人类社会不可能把“人”看成是“一样的”,而是要把人分类,这个“分类”就不是依天然因素去分,而是从“语言”上分,是从所谓“精神、思想、观点、意识”上分,同一个地区的“信徒”和“异教徒”就是典型的两类人群。社会学研究的“主体”并不是具体存在的事物,是人的“思想”,是属于“说不清的”。社会学中的概念大部分不符合“集合”原理,科学是对概念(集合)中“元素”的研究,而社会学中的概念相当多是模糊的,研究对象不是“元素”,这样的语言概念在传输中很容易产生歧义。例如,我们经常使用的“人民”这一概念,就被认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含义。社会学是把“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完全否定了是“集合”中的“元素”。例如我们说“社会主义”有多种形式,各有特色,从定义上就否定了“社会”是个科学的概念。再如“国家”一词,它对应的是一个地理位置呢?还是一个社会群体?还是一个政府呢?这些概念在使用中常常做不到是从词语概念“实”的一面去分析事物;也做不到对“说不清楚”的“虚”的一面去“沉默不语”。社会学理论不去寻找真正符合“集合”原理的“新概念”,沿用生活中常用的概念是不可能实现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
百年前五四时期就提出了“科学救国”,但没有去认真研究“科学”的本质,出现了滥用“科学”的现象。上世纪二十年代,丁文江和张君劢展开了一场关于“科学与玄学”的争论,这是很有意义的学术研究,但非常可惜这场争论由于战争等因素没有进行下去,现在看来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损失。“科学”是从语言概念的“实”出发去研究问题;而“哲学”是从语言概念的“虚”出发,去研究如何“思考”,并不对具体事物感兴趣。当时“科学”虽然在中国广泛传播,但传播的是科学技术,对如何解决社会问题不会有帮助。哲学的意义是“思维”和如何去“思维”,任何哲学原理也不可能用来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任何“思想”,无论是“科学”还是“社会学”都是“语言现象”,但“哲学”对于我们如何认识“语言”是不可少的。这里可以顺便理解一下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不了“科学”,关键就是中国过早阻止了哲学的发展,不重视语言逻辑的研究,自然产生不了“科学”!普及哲学的最好“把手”是对科学实质的学习,而不是单纯停留在科学技术上。通过学习科学来达到对“思考”的热爱,摒弃对权势的“盲从”。但“科学”一词进入中国后人们对它的认识采取了非科学的方法,只是看到了“科学技术”,并没有看到科学在哲学上的意义,没有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很少有人出来探讨一下“科学”是什么。而是利用中国语言的修辞能力将“科学”变成了一个说明某个说法或理论正确的“形容词”, 成了强词夺理的“法宝”,变成强制人们接受某种“思想”,堵塞言路的“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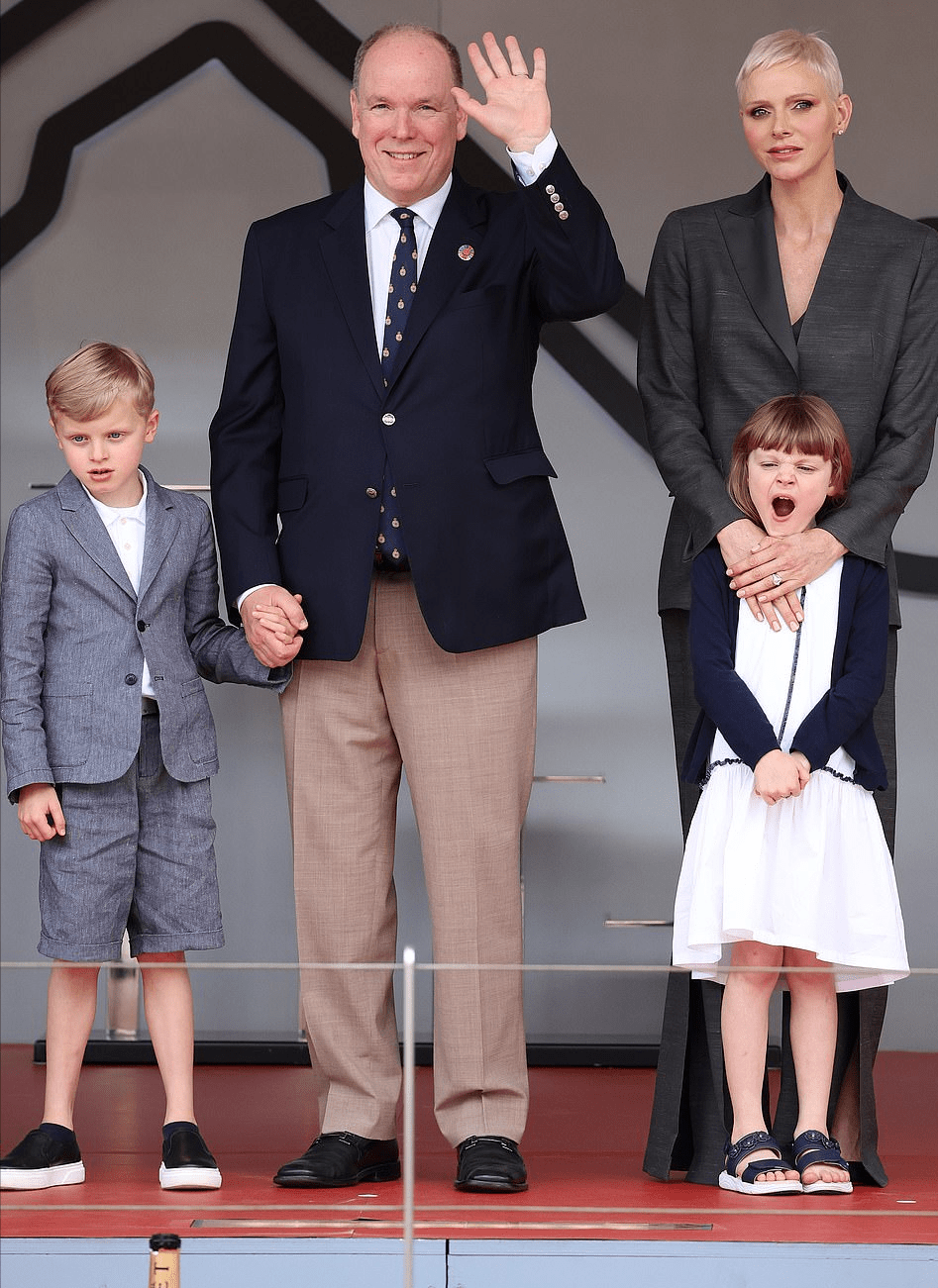

我们对“科学是什么”的研究就是对科学的哲学意义的研究,说到底是对语言逻辑的认识,知道“能说清楚的一定要去说清楚”;而对“说不清的”,一定要沉默不语。“科学”作为一个语言概念,它有“实”的一面,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识”;它也有“虚”的一面美高梅金卡高远,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尤其到了“科学”的中、高层次,“科学”脱离实际是明显的,并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科学”是一种规范使用“语言”的方法,它有这样一些要求:首先是语言逻辑就是数理逻辑,使用的词语概念是符合数学上“集合”原理的要求,研究对象是概念的“外延”而不是概念本身,不是研究“整体”问题;科学是有层次的,它的基础就是“常识”,它的中、高层次逐渐脱离了实际;“科学”不存在“验证”,但必须是可以“证伪”的。人类社会是由“语言”控制的社会,“语言”使用并不是只有“科学”这种语言方式,“科学”只是“能说清楚”的“语言”,而人类社会的历史说明,大量“说不清楚”的“语言”在管控社会。

